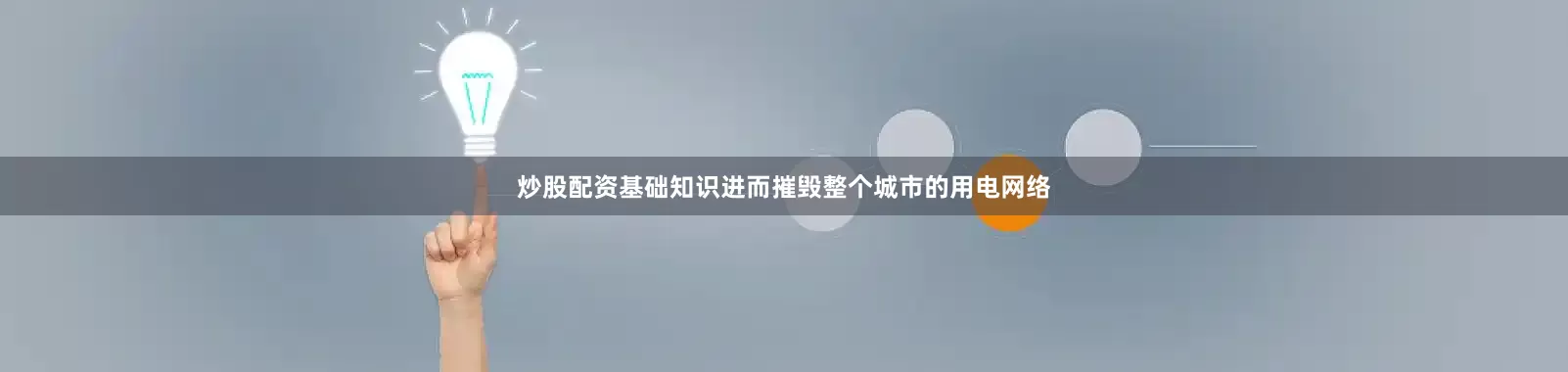原作者:愁予
注意!!未经允许禁止转载!!!
中秋皎月,清辉漫洒,月随人移。月亮始终是中秋的永恒主题,李白有诗云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,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天上地下,虽同此一月,但不仅古人今人所见之月非同一月,即便是同一人,伴随着物换星移,这所见之月亦不相同。月光所至之处,既有此处此时的喧闹,便有彼处彼时的清冷。潘钟瑞所见的八个月亮,正映射着他的不同心境。
《露台观月图》张可观 元
01 月随人移潘钟瑞(1823–1890),字圛云,晚清苏州人。潘氏乃苏州望族,他生于盛世余晖之中,早年尽享苏州的繁华富庶。现存《潘钟瑞日记》始于1860年,其中记载了他八次中秋赏月的经历。1860年中秋,太平军攻占苏州,为避战乱,潘钟瑞乘船前往上海。夜色中,一轮皓月从海面升起,此情此景,令他不由忆起昔日苏州的中秋盛景:
展开剩余92% 秉兄因念去岁中秋横塘泛月,酒绿灯红,同人扣舷,各谱《水调歌头》,一俯仰间而变迁至此,曷禁浩叹。余亦忆平生中秋望月,惟壬子舟出金陵通济门,放乎江心最为快事。潘钟瑞等人对往昔苏州中秋的怀念,虽因战乱流离而愈发深切,但苏州作为当时最为繁华之地,其中秋景象确实非同一般。简而言之,苏州人中秋喜游好宴,凡有月光处,皆人潮涌动,欢腾如昼,堪称人间胜景:
比户壶觞开宴,灯毬歌吹,莫盛于阊门内外,南北两濠,妓馆青楼,陈设更为靡丽。士女围饮,谓之专圆酒。女归安,是日必返其夫家,曰专圆节也。豪家门者,供列小擺设于几案。凡盘匜枱桌,卤簿仪仗,博具乐器,一切人间应用之物,无不缩至径寸,精巧异常,盈千累百件,无不称之。门阑士女纵观,阗聒成市,以为笑乐,名小擺设。其物非数百金不能办,仅足适观,实则一无适用,皆弃物也。自十五至十七日,每夕如是。里门夜开,金吾无禁,人在光明世界,真胜景也。《姑苏繁荣图》局部 徐扬 清 辽宁博物馆藏
中秋当日,能与月宫素娥争宠的,反而是一种叫做“小摆设”的物件。它们形制多样,精巧雅致,颇似泥塑玩偶,深受当时苏州市民喜爱。光绪十一年中秋,潘钟瑞听闻友人家中有小摆设,欣然前往观赏,并评价道“有十三桌,诸物亦取精多、用物宏矣”。阊门是苏州中秋夜的繁华核心,而虎丘亦不逊色。虎丘中秋素有“千人石听歌”之俗。千人石位于虎丘剑池外侧,是一块南向北倾斜的巨型石盘。唐代陆广微在《吴地记》中记载:“(剑池)边有石可坐千人,号‘千人石’。”中秋之夜,灯月交辉,恍如白昼,苏州百姓举家泛舟,歌舞管弦,杯盏交错,仿佛置身天上人间,不知今夕何年,“千人石听歌”由此得名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《虎邱听歌记》中,将月下虎丘的盛景描绘得栩栩如生:
凡月之夜,花之晨,雪之夕,游人往来,纷错如织,而中秋为尤胜。每至是日,倾城阖户,联臂而至。衣冠士女,下逮篰屋,莫不靓妆丽服,重茵纍席,置酒交衢间。从千人石至山门,栉比如鳞,檀板丘积,樽罍云泻,远而望之,若雁落平沙,霞铺江上,雷辊电霍,无得而状。据袁景澜记载,这般热闹景象从“十二三日始,十五日止”,持续数日方休。在这金吾不禁之夜,亦是世俗礼教稍弛之时。平日受传统约束的女子,此日亦可外出游玩,娱乐活动丰富,由此形成了“走月亮”的习俗:“中秋夜,妇女盛装出游,携榼胜地,联袂踏歌,里门夜开,比邻同巷,互相往来。有终年不相过问,而此夕款门设宴,陈设月饼、菱芡,延坐烹茶,欢然笑语,或有随喜尼菴,看焚香斗。香烟氤氲,杂以人影。街衢似水,凉沐金波。虽静巷幽坊,亦行踪不绝。逮鸡声唱晓,犹婆娑忘寐,谓之走月亮。”这欢乐的节日氛围,让女子们也体验了一番“秉烛夜游”的意趣。值此佳节,人们仿佛唯有投身于繁华热闹之中,方能尽兴。就连平日深受喜爱的园林庭院,此时也显得冷清。清代沈复芸娘曾于中秋夜游玩沧浪亭,其间亦曾提及妇女“走月亮”之俗,但沧浪亭内却几乎无一人至。
《月曼清游图》 陈枚 清 故宫博物院藏
中秋的游宴之兴,不仅从十二三日起渐入高潮,至中秋达至顶峰,节后亦余韵未绝,只是热闹的中心已从阊门、虎丘转至石湖。中秋后三日,明月依旧。苏州石湖上有座行春桥,桥有九孔。每当皓月当空,斜照桥洞,湖光倒映月影,便形成“石湖串月”的奇观。长桥两侧点缀着亭台楼阁,宛如画卷:“长虹卧波,空水映发,渔樵往来,如行画卷。吴台越垒,错置其间。高浪危风,喷薄其下。八月十八夜,吴人于此串月,书舫徵歌,欢游竟夕。金轮激射,玉塔倒悬。摇漾㳞瀜,九光十色。”苏州人云集湖上,泛舟饮酒,共赏水中连月,不知不觉间,又是秉烛夜游、通宵达旦的一日。
《石湖图页》文徵明 明 故宫博物院藏
画卷右下角便是石湖著名的行春桥,此乃石湖著名景点,曾在历代不少画家笔下现身过。
有趣的是,“石湖串月”或许仅是一个名目,苏州人来此的真正目的,恐怕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袁景澜指出,当时“书舫楼船,仅借串月之名,日间遨游山水,金乌未坠,便已辞棹石湖,争泊白堤,传觞醉月矣”。这与潘钟瑞在光绪十三年的记载如出一辙:
余即作札,遣人往约明日回札。伊有今日石湖之兴,但未有船,姑往与商。伊遂拉余同出胥门,在万年桥一带觅船,得一圈棚小船于板桥头,说定雇价,买些点心带去。放棹已是正午时。喜得舟小速,又张片帆,至石湖边上泊定,煮面食之以代饭。拟再前行,则他舟已陆续转棹。前则逆势,退则顺流,乃亦退。但见画船衔接,篙橹如沸,诧为良辰盛事。盖向来行春桥看串月为吴中闹市,今大小快船借此为名,作酒地花天之会,而绝无停待至夜、看过月升而归者。故夕阳正好,已匆匆转棹。余亦随他归去,仍在桥边登岸。进城,就来远桥小茶馆茗饮,歇息片刻,散。可以发现,潘钟瑞放棹是在正午时分,其在石湖上漂泊,日暮时分潘钟瑞还想泛舟前进时,湖上的大小舟皆已返航,导致潘钟瑞等人亦停滞不前,只能返航,此时正是夕阳时分,素娥未出,大家便已尽兴而归。潘钟瑞也认为所谓的石湖串月,仅是“今大小快船借此为名,作酒地花天之会,而绝无停待至夜、看过月升而归者。”
《石湖图》局部钱榖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,这般中秋盛景乃是常态。彼时潘钟瑞正值年少,出身世家,“吴门年少好事多,分曹结对斗笙歌”,自然不会错过此类盛会。的确,见识过苏州中秋的极致繁华后,寻常地区的中秋便显得索然无味。更何况1860年的苏州因战火而凋敝,胜景不再,物是人非,潘钟瑞心中生出凄凉之感,亦是必然。
02 月淡心闲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,潘钟瑞结束漂泊,重返苏州。现存的《潘钟瑞日记》多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录,此时的潘钟瑞已入暮年,不再是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,因而他笔下的中秋节,也褪去了昔日的繁华喧嚣。在多年的日记中,有两件事他始终提及:一是赏月,二是“荐新”之俗。荐新,即以时鲜祭品供奉祖先。此俗未见于《清嘉录》《吴郡岁华记丽》等方志,从潘氏日记来看,这或许是潘氏宗族内部特有的传统。
除赏月、荐新外,潘氏日记虽少有记载其他习俗,但苏州人在中秋日的活动实则颇为丰富。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记载了一种特殊风俗:月出后,于庭院中陈列花瓶烛台,让孩童向月跪拜,嬉戏灯前。据说此俗在北京亦有,但更为复杂:“中秋之夕,人家各置月宫符像,符上兔如人立。陈瓜果于庭,饼面绘月中蟾兔,男女肃拜烧香,旦而焚之。”不过顾禄明确指出,吴地风俗仅为“对空膜拜”。但到袁景澜的时代,情况似乎有所变化:
吴俗中秋人家各设炉香灯烛,供养太阴,纸肆市月光纸,绘月轮桂殿,有兔杵而人立,捣药臼中,极工致。金碧璀璨,为缦亭彩幄,广寒清虚之府,谓之月宫纸。又以纸绢为神,具冠带,列素娥于饼上,谓之月宫人。取藕之生枝者,谓之子孙藕;莲之不空房者,谓之和合莲;瓜之大者,细鲠如女墙,谓之荷花瓣瓜。佐以菱芡、鲲杏之属。以纸绢线香,作实塔形,钉盘杂陈,瓶花樽酒,供献庭中,儿女膜拜月下。拜毕,焚月光纸,撤所供,散家人必遍。嬉戏灯前,谓之斋月宫。袁景澜笔下的“斋月宫”显得更为复杂精致。“斋月宫”即祭祀月亮,祭品包括绘有广寒宫的“月光纸”、饰以嫦娥的“月宫饼”,以及寓意吉祥的“子孙藕”、“和合莲”等。祭祀时,将这些供品与香烛酒樽一同陈列庭中,对月跪拜,而后焚化月宫纸。整个过程庄重而不失趣味,既敬神,亦娱人。其中,“月宫饼”与塔形线香尤值注意。“月宫饼”即月饼,在清代已成为中秋首要节物,种类繁多:“中秋节物,以月饼为先,市里卖饼之家,名茶食店。大小形制不一,以糖活粉为之。其馅有豆沙、玫瑰、蔗糖、百果各种,人家争先置买,馈贻亲戚。十五夜,则偕瓜果,以供祭月筵前。”
《拜月图》佚名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画卷中央的紫衣女子,正双手合十,诚心祷拜,其面前摆放着香炉
斋月宫时燃烧的实塔形线香,实际有专门的名称——烧香斗。这种香斗一般是以线香缠绕成斗状,再纳香屑于其中,并在香斗中间插一株塔香,据说此香“僧俗皆买之,焚于庭中月下”。焚烧时,“儿女杂坐其间,剥菱食芡,笑语喧闻,香烟缥缈,坐待香残,则灯炧月斜,夜已深矣。”如果说阊门、虎邱和石湖的中秋夜月是繁华喧嚣的,那么斋月宫、吃月饼和烧香斗时的庭中之月,洗去喧嚣之气后,素娥回归朴素,反而更显温馨、有趣。亲朋好友围坐一堂,天上月圆,低下团圆,道是平常也非常,毕竟苏轼此等超然之人,亦不免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月缺”的遗憾。
《嫦娥月宫图》刘松年(传)南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03 秋宵月澹潘钟瑞一生坎坷,除历经太平天国之乱,中年又遭丧偶之痛。步入晚年后,他逐渐皈依佛门,心性趋淡。因此,在其晚年日记中,再无前往阊门、虎丘等热闹之地过中秋的记载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淡闲适的生活意趣。如光绪十年八月十五日,潘钟瑞时在苏州:
雨,乘轿至松鳞庄祠,族中到者寥寥,辛芝弟到过,不值。余少坐,归家,即遣轿夫去。在家坐雨,料理节事,亦甚闲闲。筱兄案头有《夜谭随录》,阅之,尽两本。候至傍晚荐新祖先前,展拜毕,笠返馆,雨止无月。正如上述所言,光绪十年的中秋节,潘钟瑞过的格外平常,除了傍晚前往展拜祖先外,其余大多时间都在家,并未有其他的举动。虽然说有下雨的缘故在内,但在其晚年的日记中,这种疏松平常的中秋节乃是常态。又如光绪十三年的中秋节:
清晨,诣庄祠拜祖,并见族中诸人道贺,又以名片遣人往洪家道谢步。既出,却在间壁寻得江建霞。进见之。快谈,得遍观其所收金石拓本,可云富有。又见清卿中丞与之通札,皆作古篆,得未曾有。良久,出。至铁翁家,亦移晷谈。辞出,尚有午后之约。余至敏德午饭,观屈氏昆弟与人作竹园游。良久,到观中,铁翁已在。啜茗吃菱,谈久之,傍晚乃散。归家,为祖先前荐新,展拜毕,返馆,抵暮。《赏月图》冷枚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除了祭祖以外,潘钟瑞在中秋节最大的兴趣似乎便是到处走访朋友,蹭饭闲聊,赏月饮酒,光绪十一年的中秋节,可谓是潘钟瑞晚年中过的最热闹的一次:
早出,至敏德少坐,与元吉同出至观门口分路。余至庄祠,与辛弟话,伊先去。余至铁翁家闲谈,又同至玉寿仙茶叙,晌午乃散。归家午饭,兄偕永侄往光福,只与松兄话。承钧侄孙捧出其父乡试头篇文呈阅,尚未送先生处,余缀评纸尾。敬弥勒佛龛联于邻寺,亲自过去,看人悬挂。返家,松兄小睡,更无人谈。遂出,由养育巷行,遇茶磨于友石处,方对酌,旁有陆晓云者,亦谈天客也。茶磨于酒边赠友石一律,起句云“君是高阳一酒徒市中大隐见真吾”,盖索酒契也。尽一觥起,拉余至茶寮,云与同人有约。少时,仓石来。少时,心兰来。余返馆取小坡扇面,一交还心兰,一索其画《壶园饯春图》。谈次,友石、晓云皆来,吴颖芝亦来,团坐圆桌,谈及仓米巷南口陈恒升家有小摆设,盍往观之。于是先后皆往惟仓石别去。陈处摆设年盛一年,有十三桌,诸物亦取精多、用物宏矣。返馆,铜士设酒,与账房诸公赏中秋,既而月出,墙阴花影,离离如画,凭窗坐对,移时就睡。《山斋赏月图》李唐(传)南宋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
这一天,潘钟瑞兴致极高。从清晨起便四处访友,先后至敏德、铁翁、松兄等处,品茶对酌,不亦乐乎。中午仅回家匆匆用餐,之后又携侄访友,并抽空至寺庙敬献佛龛。再访友人时虽遇其小憩,他却并未扫兴,转而另寻友人对酌谈天,还一同去观赏了友人的“小摆设”。直至日暮归家,往年此时他多已准备就寝,但此番恰逢有人设酒赏月,他便再次加入,直至深夜方歇。从早到晚,他几乎都在访友途中,虽未涉足阊门、虎丘等喧嚣场所,但在其晚年的中秋里,这已是难得的热闹景象。
潘钟瑞最后一次看见中秋月是在光绪十五年。据潘钟瑞记载,这天本是阴雨绵绵,但午后天气渐霁。傍晚,潘钟瑞参加宴会,结束后正解衣欲睡时,方见窗外月上。
次年,潘钟瑞溘然长逝。
04 结语结合《潘钟瑞日记》和其他文献,可以清晰地发现中秋节的多元面貌:它既是阊门内外万人空巷的喧闹与石湖之上画船箫鼓的欢腾,也是自家庭院中斋月宫、烧香斗的温馨与清寂。潘钟瑞青年时,他追逐的是“千人石听歌”的热烈喧嚣;晚年时,他安享的是与友人品茗闲谈、静观“墙阴花影”的个人闲适。他的心境从热烈归于平淡,所见的月亮也便从繁华的映照成为了安宁的陪伴。中秋的月光从未改变,改变的是赏月之人与人生阶段,但幸好无论喧闹还是清冷,我们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圆满。
参考文献:
1.(清)顾禄:《清嘉录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9年。
2.(清)袁景澜:《吴郡岁华纪丽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年。
3.蔡利民:《苏州民俗》,苏州:苏州大学出版社,2000年。
4.潘钟瑞著,尧育飞整理:《潘钟瑞日记》,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19年。
5.沈复等:《浮生六记(外三种)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。
发布于:江苏省实盘配资平台有哪些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